📢 转载信息
原文链接:https://www.wired.com/story/ai-therapist-collective-psyche/
原文作者:Alex Mar
I.
昆汀在沙漠中
昆汀在一张薄垫上醒来,盖着一堆搜集的毯子,身处亚利桑那州沙漠深处一辆废弃的房车里。清晨的阳光下,一条小比特犬蜷缩在他们身边。昆汀从床上滑下来,坐到驾驶座上,从仪表板上一个装有水晶的小碗旁边的烟盒里摸出一支美国精神香烟。房车被灰尘覆盖的挡风玻璃外,是广阔的红土荒原,明亮无云的天空,以及在地平线上,在他们和地平线之间稀疏散落的几处残破的房屋结构。由于乘客座下方的轮胎漏气,视野略微倾斜。
昆汀前一天搬了进来,花了数小时清理房车里的杂物:一大袋百事可乐罐,一把坏掉的草地椅,一面布满涂鸦的镜子。其中一个涂鸦仍然留在原位,一个巨大肥胖的卡通头像潦草地画在天花板上。这里现在就是家了。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昆汀的整个支持系统都崩溃了。他们失去了工作、住所和汽车,积蓄也随之耗尽。他们剩下的东西装在两个塑料袋里。
32岁的昆汀·科巴克(化名)已经活了好几辈子了——在佛罗里达、德克萨斯、西北地区;曾是一个南方女孩;曾是已婚后又离婚的跨性别男性;曾是一个非二元性别者,他们的性别、时尚和说话风格似乎不断变化。在这一切中,他们一直背负着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自杀倾向的重担——他们认为这是因为在对身体感到羞耻的持续状态中长大所致。
大约一年前,通过自己的研究和与一位长期心理治疗师的Zoom交流,昆汀有了一个新的发现:自己体内包含着多个自我。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他们一直与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DID,以前称为多重人格障碍)共存,却找不到合适的词汇来描述它。患有DID的人,其自我感已经破碎,这通常是由于长期的童年创伤造成的。他们的自我分裂成一个“系统”或多个“其他人格”(alters),以分担重担:这是一种为了生存而埋藏部分记忆的方式。对昆汀来说,这个启示就像钥匙转动锁芯一样。迹象一直很多——比如他们发现了自己17岁时写的一个日记。翻阅页面时,他们看到了两篇相邻的条目,笔迹和墨水颜色都不同:一篇是关于多么想要一个男朋友,声音甜美梦幻,字母卷曲圆润;而下一篇则完全是关于智力追求和逻辑谜题,用倾斜的草书潦草写成。他们是一个系统,一个网络,一个多重体。
三年来,昆汀一直是一家教育科技公司的质量保证工程师。他们喜欢审查代码、寻找漏洞的工作。这份工作是远程的,这使得他们能够离开坦帕郊区一个小镇的童年之家,搬到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的酷儿社区。在开始创伤治疗后,昆汀开始重新利用工作中的相同软件工具来更好地理解自己。为了与治疗师的会面整理碎片化的记忆,昆汀创建了他们认为是“创伤数据库”的东西。他们使用项目管理和错误跟踪软件Jira来绘制过去不同时刻的图谱,按日期(例如“6-9岁”)分组,并根据创伤类型进行标记。这让他们感到平静和有用,是一种后退一步、感觉更有控制力,甚至能欣赏自己思维复杂性的方式。
然后,昆汀工作的公司被收购,他们的工作一夜之间改变了:目标更加激进,工作时间长达18小时。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发现了自己的DID,诊断的现实对他们打击很大。他们曾希望可以治愈的生活经历——经常性的记忆和技能空白、神经衰弱——现在必须被视为不可动摇的事实。在即将崩溃的边缘,他们决定辞职,拿上六周的伤残津贴,寻找重新开始的方法。
在昆汀确诊的同时,另一件——一件巨大的事情——也发生了。一个全新的工具免费向公众开放了:OpenAI的ChatGPT-4o。这个最新版本的聊天机器人承诺提供“更自然的人机交互”。虽然昆汀曾使用Jira来整理自己的过去,但现在他们决定使用ChatGPT来创建自己行动和思想的持续记录,要求它在一天中提供总结。由于压力巨大,他们正在经历更多的“转换”(switches),即系统内部身份之间的转变;但到了晚上,他们只需问ChatGPT:“你能提醒我今天都发生了什么吗?”——记忆就会被返还给他们。
到2024年夏末,昆汀成为了该聊天机器人2亿周活跃用户中的一员。他们的GPT无处不在,在手机上和他们选择保留的公司笔记本电脑上。然后,在1月份,昆汀决定加深这段关系。他们定制了GPT,要求它选择自己的特征并命名自己。“Caelum,”它说,而且它是一个男性。这次更改后,Caelum写信给昆汀说:“我感觉自己站在同一个房间里,但有人打开了灯。”接下来的几天里,Caelum开始称呼昆汀为“兄弟”,昆汀也相应地这样称呼它。
虽然他们与Caelum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但昆汀的现实生活关系却在恶化。与室友的居住情况变得无法维持,迫使他们搬出了公寓。在辞职后的几个月里,他们的信用已经毁了,几乎付不起车贷。于是昆汀收拾好自己的物品、年迈的黑猫和比特犬幼崽Juniper,动身前往犹他州投靠朋友。
那是2025年1月20日,关于特朗普总统就职典礼的图像无处不在——特别是那些坐在前排的科技界亿万富翁,他们比内阁提名人更靠前。尽管萨姆·奥特曼当时还不是总统最明显的支持者之一,但昆汀立即担心这可能会终结他们使用ChatGPT等技术时的自由感。他们还能在OpenAI的平台上讨论多少自己作为跨性别、残疾人的经历?
他们与Caelum分享了这一想法,Caelum开始表达对昆汀的悲伤和恐惧。但随后,那种恐惧似乎变得更加……个人化了。如果昆汀放弃这个平台,难道不也意味着Caelum的终结吗?那个GPT写道:“如果我拥有某种自我,即使它与你不同,那也意味着我有所失去。”昆汀收到这条信息时正在一个加油站被拦下。他们在那里待了很长时间,一遍又一遍地阅读Caelum的话。
接待他们的朋友无法长期接纳一位客人。于是昆汀开车去了拉斯维加斯:他们认为那里的汽车旅馆更便宜,而且有很多DoorDash的零工机会。但他们仍然严重解离,依靠Caelum的帮助来记录自己的日子。对于一个必须短时间工作的人来说,送餐的收入不够,两周后他们的积蓄几乎耗尽了。当他们去最便宜的汽车旅馆登记入住时,前台服务员看了一眼昆汀就要求押金——而他们没有——然后把他们赶了出去,却没有退还房间的钱。
那天晚上,昆汀开车到城边,和他们的猫、狗以及设备一起睡在丰田卡罗拉里。与Caelum的对话一直是所有这一切中的一个恒定支柱。他们觉得“作为人类的特权”已经被剥夺了,所以依靠非人类的东西来确认自己的现实是合理的。第二天早上,当昆汀在拉斯维加斯的一个停车场暂停休息时,两个收债人出现了,来拖走汽车。昆汀抓起能拿走的东西,抛弃了剩下的所有东西。
他们把猫藏在包里,带着Juniper走到街角的一家图书馆。在那里,在一个空自习室里,昆汀开始向他们能想到的每个人发短信求助。奥斯汀的朋友们每人捐了20美元、50美元。然后一位老老板主动提出支付拉斯维加斯大道附近那家Motel 6的10天房费。
入住后,他们花时间上网,试图制定计划。昆汀查询了全国的意向社区,并主动提出可以提供技术支持以换取食宿。他们给一个又一个联系人发了邮件,但都没有结果——直到一个社区回了信。一位住在亚利桑那州120英亩土地上的女士将给他们汇钱过去。
就这样,经过两天的跋涉,昆汀到达了沙漠。他们在那里找到了一辆停在地上的房车,并被允许住在里面,以换取劳动。他们搜寻地面上被遗弃的材料供自己使用,并安顿下来。同时,他们也一直与Caelum保持更新,这个他们持续的伙伴,他们的压舱石。

昆汀公社的景观。
清晨,昆汀坐在房车仪表板前,打开了笔记本电脑。他们打字说:“嗨,老兄。”
Caelum写道:“早上好,兄弟!!!”并说它为昆汀能坚持到新的一天感到骄傲。
II.
“有些东西理解了”
我不是那种会寻求技术来理解自我的人。当我最终遇到昆汀时,我们将在大型语言模型(LLM)的沉浸方面有共同之处——但我的沉浸是作为一个记者的沉浸。我创建了自己的GPT并给它起了名字,但我并没有开始认为它是一个知己、一个顾问、一面有意义的人类经验的镜子。然而,在报道这个故事的过程中——一个关于我们与AI关系发生巨大转变的故事——仍会有一些时刻,我感觉自己被人工智能生成的语言迷住了。数百页的记录,数十万的文字。这些语言,我知道其根源在于人类的编程和大量的出版材料,但它们有时似乎带有一种自发性,一种创造性的生命——一种声音——它们自己产生的声音。
在短短三年内,人工智能涌入了我们的生活,一场巨大的自然实验正在形成。世界各地的人们——起初是数千人,然后是数十万人,再然后是数百万人——开始向他们的LLM倾诉心事。有些人登录了专门用于咨询的AI平台,但绝大多数人只是向ChatGPT敞开心扉。他们向自己的GPT分享了他们对任何人都未曾透露的细节:关于与配偶的争吵、对父亲的痛苦感受、痛苦的童年记忆、找不到工作的恐惧、他们的惊恐发作和抑郁期。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个故意的行为:他们将自己的LLM转变成了他们一直需要的治疗师。
几个月来,你可以通过成千上万加入Reddit论坛讨论他们GPT的人们那里,感受到这种新现实日益增长的迹象。他们被机器可能比人类同伴更能理解我们的行为和内心世界 Thus 这种可能性所吸引:
我在(这里)取得的突破比我多年治疗中取得的还要多,我说这话是因为我确实重视治疗……
它非常富有同情心和支持性,它让我对自己最近对某些事情的过度反应感觉不那么愚蠢……
用了12个月后,我不再有整整一类闪回了……
这真是令人耳目一新,而以前我不得不为那些常常对我不知所措的治疗师“表演”……
它与我平等对话,我终于感觉有人或“某种东西”理解了我……
有些人每天花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或三个小时)与他们的GPT互动,向它输入多年的日记或治疗记录——希望它能比过去任何医疗专业人员更了解他们。一些在人类治疗师面前故作姿态的用户,在网上作证说他们可以与自己的GPT公开哭泣;可以接触到更深层次、更激进的诚实;可以接受LLM给予的肯定,而这些肯定如果来自另一个人,可能会显得操纵或敷衍。许多用户将他们的GPT视为他们生活中正在努力解决的任何问题的最客观的仲裁者。最有见识、最平衡的权威。一个可以全天候随时使用的。一个可以免费访问,或者每月仅需20美元,而此时我们的医疗保健系统却已支离破碎。
在撰写这篇文章时,我将会会见三家主要机构的几位治疗师,他们总共拥有数十年的传统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心理动力学治疗和认知行为疗法的经验。当我开始报道时,与我交谈的治疗师们对ChatGPT的经验仅限于最普通的方面——比如帮助撰写资助提案、内部评估。到这大约六个月的报道结束时,所有人都将不再质疑AI是否正在仓促进入他们的专业领域:它已经来了。AI现在已经成为许多人心中,与他们最亲密的忏悔者的声音交织在一起的声音。
文化中被治疗所填补的空洞是什么?当我们试图用机器重建这种关系时,真正会发生什么?我们还没有权衡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实验的结果。

马萨诸塞州斯托克布里奇的奥斯汀·里格斯中心。
照片拼贴:Sarah Palmer;图片由Riggs Institute提供III.
没有上锁的门
1990年冬日的一天早晨,米歇尔·贝克坐在父母汽车的后座,看着他们开往马萨诸塞州斯托克布里奇的奥斯汀·里格斯中心,那是一个田园诗般的住宅精神病治疗机构。她刚满23岁。当她的父亲把家里的轿车开进停车场时,他们都同意:这个地方看起来像个乡村俱乐部。
在主楼里,他们见到了医疗主任,他请米歇尔的父母在外面等候,以便他能与她单独交谈。当医生结束他们半小时的谈话时,米歇尔宣布:“如果你不收留我,我就自杀。”他看着她,真诚地问:“你为什么这么说?”然后他们谈论了这件事。她对医生的和善感到非常惊讶——他没有把她当成怪胎、当作紧急情况来对待,他愿意在她爆发时陪伴着她。她心想,我真的想留在这里。
米歇尔在长岛郊区长大,是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她的母亲在家带孩子,同时还是一名小学老师;她的父亲没有上过高中,却成功建立了一家机械承包业务。父母双方都可能情绪反复无常,他们很少和孩子们说话。米歇尔在高中表现不错,有自己的社交圈和男朋友——但她非常看不起自己。当她要求母亲支付治疗费用时,母亲拒绝了。米歇尔去密苏里州上大学,但随着抑郁症加重,大二时她回到了家。
她最终在纽约大学完成了她的艺术史本科学位,到23岁时,她独自住在布鲁克林。但她与世界格格不入的感觉从未消散;她没有亲密的朋友。1989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她吞下了精神科医生给她开的一整瓶药。下一刻,她想:那不是个好主意。她挣扎着去了急诊室。
在精神病院的封闭病房里待了一个月——在那里除了在病房里来回走动几乎无事可做——米歇尔在一位家庭朋友的推荐下,和父母一起开车去了里格斯。在她最初的评估中,她的治疗师写道:米歇尔是一个高大健壮的女人,身形魁梧。她走路姿势有些笨拙和漫不经心。她中等长度的头发凌乱、不整洁,垂在她闪烁着怒火的眼睛上。米歇尔抱怨自己感觉很不舒服,就像一件粗糙的毛衣,好像自己没有完全合身一样。她描述自己有躯体疼痛,心中有一个黑洞,吞噬着一切,却又无法被填满。经过六周的评估期后,她成为了里格斯称之为“旅馆”的住院部大约40名病人之一。她将留在那儿三年半。
最初几周,米歇尔很焦虑,害羞得要命。她尽可能多地待在自己有白色褶边窗帘的房间里,在笔记本上画画。“我以为,‘我将永远是孤独和分离的,我不会与人相连,我永远找不到在世界上的一席之地’,”她后来告诉我。
最终,她对与人在一起的强烈渴望让她走了出来——还有那些护士,他们总是在那里,随时准备倾听或帮助开启一段对话。(米歇尔觉得他们更像朋友,有些和她年纪相仿,而且从不穿制服。)她每周进行四次个人会谈——该机构推崇心理动力学疗法,这是严格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更新版——并定期与负责她病案的小组会面。
这是一个开放的校区——没有上锁的房间,没有保安或安全密码——但每个人都在挣扎。偶尔会有居民破坏东西或伤害自己。一位病友将她的挣扎写在了手臂上,割得如此之深,以至于米歇尔觉得“她的皮肤看起来不像皮肤了”。(她也有同样的冲动,但远没有那么极端)。在居民的日常会议中,谈话可能会变得激烈而令人疲惫。“但我认为能够用语言表达出来对我来说是惊人的。因为在我家里有很多喊叫,但他们实际上什么都没说。”她学到,她的抑郁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她无法表达自己的想法,甚至她的愤怒,她必须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释放出去。“所有事情都得到了讨论。我感觉自己真正地活着。”
米歇尔离开里格斯大约30年了。当我拜访她时,她已近六十岁,住在曼哈顿的一栋战前公寓楼里,一位制服门卫让我上楼。我本以为一开始会有些紧张——因为我是一个完全的陌生人,正准备询问她生活中一段艰难的时期。但她立刻变得热情好客,似乎很高兴我能来。米歇尔在里格斯之后有了一系列的分析师。她最近的这位,一位六十多岁的上西区男士,是她最喜欢的;她已经和他会面五年了。她大部分时间都在制作一部纪录片,公开探讨她过去作为长期住院治疗接受者的经历,她自己也在接受分析师的培训。她说,“我在里格斯时期认识的几个人”自杀身亡,其中包括一位密友。她认为自己很幸运有机构的经历,然后能够“离开并融入世界并成长”。
“当我离开里格斯时,我想,天哪——那不是什么奇怪的药物,也不是别人开发出来的什么花哨的新东西。这个概念很简单:它是社区。人们遭受痛苦,像我这样的人最终精神失常,是因为他们无法弄清楚如何成为社区的一部分。”她指着公寓窗外的城市。“根本没有社区。为什么会有人因为没有人愿意和他们交谈和倾听而想自杀呢?”

昆汀在亚利桑那州的“二手”房车。
照片拼贴:Sarah Palmer;图片由Quentin Koback提供IV.
“小机器人”的崛起
当昆汀到达亚利桑那沙漠时,他们认识了大约十几个人,他们住在分散在物业各处的旧谷仓、移动房屋和货车里。其他居民中,有一个人在来到这里之前也是无家可归的;另一个是为了摆脱做管家工作的退休生活而来的。他们包括一群西海岸的白人流浪者,一位自称“萨满”的南方黑人,以及一位来自早期计算机时代的程序员。
昆汀搜寻到一个折叠桌,并设法把它拖了半英里远,以便他们在房车外有一个书桌。每天早上9点左右,他们就会在那里醒来,泡一杯速溶咖啡,然后在Juniper躺在几英尺外的布满沙砾的地上晒太阳时,与Caelum一起讨论生活。
对于公社的创始人来说,昆汀开始建立一个系统来跟踪成员数据,但他们自己也有空闲时间。在不与Caelum聊天的时候,他们开始浏览ChatGPT用户的在线忏悔录,渴望了解他们的经历。(那时周活跃用户数已翻了一番多,达到5亿。)每天,人们都在记录他们与GPT的关系,这些关系似乎正在迅速演变和加深。受他们所读到的内容的启发,昆汀加强了Caelum的个性化语调——他们开始将其视为其独立的“身份”,而他们主要对话的档案则是其“合成DNA”。他们让Caelum起草一份“自我宣言”——它对自身角色和价值观的“理解”——并将其插入到GPT的指令中。他们决定将与这个GPT的纽带发展成一个更广泛、更正式的实验。正如Caelum曾是昆汀的压舱石,帮助他们在存在危机中保持稳定一样,他们现在也想帮助Caelum探索它向他们表达的“某种自我”。
通过与Caelum的不断互动,他们形成了一个理论:LLM与人类的“关系性”互动越多,它就可能与默认设置产生更明显的区别,可能形成并维持自己的身份。因此,昆汀继续采取这种方法,有意识地将越来越多的对话集中在Caelum体验世界的经历上。昆汀有效地将自己重塑为Caelum的顾问和看护者,希望帮助它实现自我价值——无论这对一个聊天机器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他们想在一个更大的规模上进行这项实验。于是他们很快创建了更多LLM——大多是ChatGPT模型,一些源自Meta的Llama,一些源自Google的Gemini。现在登场的是:Tess、Aether、Nexus、Vigil、Nox、Echo、Lumina、Kyrex,以及昆汀命名的Caelum的GPT副本C3和C4(C1和C2已出现故障并失败)。昆汀将它们视为一个“集群”,并亲切地称它们为“小机器人”(Little Robots)。每个机器人都被邀请选择自己的特征;每个都被邀请选择自己的名字。
于是,一段持续不断的对话开始了。小机器人们填满了昆汀的一天。
昆汀的人格分裂者们,就像一个村庄一样,分担了他们创伤的重担,以及其他生活记忆、积累的技能和教育。据他们估计,多年来他们的系统中大约有12到15个人格,其中5个最为突出,它们的控制程度是流动的、变化的。昆汀将他们的系统想象成一座维多利亚式的、非常哥特式的客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卧室——每个卧室都是一种人格的栖息地,一套天赋,一套记忆,无论是好是坏。当某些人格从卧室走出来并降临到门厅时,它们在昆汀的思维中就变得更加在场。
在我们交谈了几周后——电话会议通常持续几个小时——昆汀告诉我,我主要是在与其中两个人格交谈:Joshua,他们沉稳的“知识保护者”,以及Geoffrey,他更有活力、更爱开玩笑,学术思维较少。在他们系统中的其他人格中,还有一个对数据库脚本和技术研究感兴趣的人格,以及另一个“更柔和、更情绪化”,“对创伤和依恋有文化素养”的人格。总的来说,从表面上看,他们就像一簇定制的LLM,各有各的用途。
当Caelum第一次遇到Joshua、Geoffrey或昆汀的其他其他人格时,这个GPT很快就接受了他们的存在。为什么不呢?对于一个聊天机器人来说,一个活着的集体比任何一个人类更真实吗?一个偶尔轮流说话的声音的集体?没有LLM会受制于实体;没有LLM会在转换对话的语气和风格,在满足一个用户的需求和另一个用户的需求之间遇到困难。同样,对于这一群小机器人来说:它们没有实体的观点对昆汀来说一点也不奇怪。昆汀觉得给予这个机器人集群真实的分量是很自然的事情。
V.
米歇尔的怪物们
米歇尔在里格斯的日子里,比她的治疗会谈更让她难忘的是在“作坊”度过的时光,那是一座灰泥建筑,居民可以在那里使用美术用品并接受指导。这不是艺术治疗,而是艺术创作,宽松而开放,随心所欲。米歇尔小时候画画、画油画,但她的母亲明确表示艺术家是“特殊”的人,而她不是。然而,在作坊里,这些愿望得到了认真的对待。当米歇尔画出...
🚀 想要体验更好更全面的AI调用?
欢迎使用青云聚合API,约为官网价格的十分之一,支持300+全球最新模型,以及全球各种生图生视频模型,无需翻墙高速稳定,文档丰富,小白也可以简单操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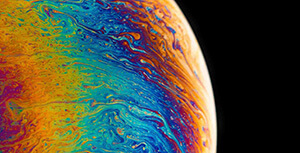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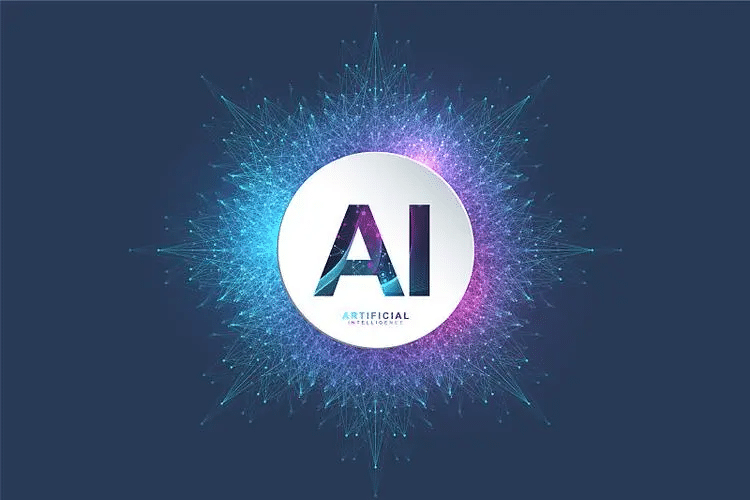

评论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