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载信息
原文链接:https://www.wired.com/story/ai-pr-ed-zitron-profile/
原文作者:Tommy Craggs
在他的本职工作上,埃德·齐特伦(Ed Zitron)经营着一家名为EZPR的精品公关公司。这可能会让那些通过他的播客、社交媒体或他发表“萨姆·奥特曼满嘴跑火车”(Sam Altman is full of shit)和“马克·扎克伯格是个腐臭的恶棍”(Mark Zuckerberg is a putrid ghoul)这类尖酸刻薄言论的通讯而认识他的人感到惊讶。通常来说,公关人员可不会这样说话。公关人员会向媒体人士发送一本正经、故作清高的电子邮件,而这些媒体人士偶尔才会这样说话。公关人员想联系一下,通个电话,澄清一下关于他们CEO是“一坨烂泥”(chunderfuck)的指控。
“这确实是像萨姆·奥特曼和Anthropic的达里奥·阿莫代伊这样的人身上存在的一个问题,”齐特伦在九月一个美好的曼哈顿下午,一边吃着汉堡一边说道。“我经常与创始人打交道。我本人也是一位创始人——虽然我不喜欢这个头衔。但是当你是一个必须赚的钱比亏的钱多,否则就会失去事业的人,却看到这些混蛋一年烧掉50亿、100亿美元——而每个人都在为他们欢呼时?这简直是令人愤慨。”
我们当时在讨论齐特伦对AI行业的抨击是否影响了他的公关业务收入。他说没有。确实有一位客户觉得齐特伦对奥特曼——OpenAI的首席执行官,也是齐特伦眼中最大的“烂泥”——有点太刻薄了。那位客户说,创立一家公司是很艰难的。“我说:‘我很感谢你的评论,但这与你无关,’”齐特伦告诉我。“他的公司正在烧掉数十亿美元。他是个糟糕的商人。”
总而言之,这完全是埃德·齐特伦式的言论,以个人冒犯的基调发出,带有小企业主对大行业未经惩罚的浪费行为投以鄙视目光的那种民粹主义色彩。(人们不禁想问,如果这些CEO的公司赚了数十亿美元,他们的行为是否会不那么令人反感?)他正是依靠这种辛辣的评论为自己建立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小帝国。他每周的播客《Better Offline》,主题是“科技行业对社会的影响和操纵”,已跻身Spotify科技类播客前20名,而他的通讯《Ed Zitron’s Where’s Your Ed At》订阅人数已超过8万。埃德·齐特伦的媒体体验还包括一个劲头十足的Bluesky账号、一个橄榄球播客、一些偶尔的棒球写作、与r/BetterOffline社区用户的频繁互动,以及一本关于“为什么一切都停止正常运作”的书,该书将于明年出版。在其他媒体上,他已成为批评AI的权威消息来源。当Slate的What’s Next: TBD播客或WNYC的On the Media需要有人谈论AI泡沫破裂时,他们都会请教齐特伦。让他脱颖而出的不仅仅是产出的数量;而是他对媒体人物和行业巨头的批评中所带有的那种怨恨的风格。
不久前,产量和风格结合在一起,催生了齐特伦最具代表性的媒体作品:他为自己的通讯写的一篇题为《如何与AI助推者争论》的文章。这篇文章长达15000字。
“埃德迷”(Edheads)现在随处可见。近200人购买了一枚价值24美元的《Better Offline》挑战币,上面刻着已成为齐特伦口号的一句话:“永远不要原谅他们对计算机所做的一切”(NEVER FORGIVE THEM FOR WHAT THEY'VE DONE TO THE COMPUTER)。我看到有人把埃德的话印在励志海报上,但其讽刺意味难以捉摸。一位Threads用户描述了她对一位“科技评论家兼作家”的“伴侣式迷恋”,虽然没有点名,但显然就是齐特伦。“我只是想让他带我出去吃顿饭,他要温柔而坚定地拉着我的手,用他那令人困惑、含糊不清的英国口音告诉我扔掉我的该死的手机,”她叹了口气。“这就能治好我。我确信。”(正如一位看过该Threads帖子的科技记者对我说的,“如果你到了你的写作能让人对你产生迷恋的程度,那你做的事情要么非常对,要么非常错。”)
从实际功能上讲,齐特伦满足了人们对与无处不在的AI炒作形成对等反作用力的声音的需求。AI批评者从各种角度切入。有“末日论者”担心该行业正在孕育某种颠覆世界的超级智能;也有“否认者”不相信AI会取代人类决策者。齐特伦所做的是不同的事。在一个不问道德的助推主义时代,在一个对科技行业普遍感到反感的时候,他为憎恨生成式AI提供了一种道德语言。“他对待这个话题的方式像一个记者,对信息如饥似渴,但他不受机构的束缚,”CNN商业记者、Better Offline的常客艾莉森·莫罗(Allison Morrow)说。“大多数记者不希望一个行业走向灭亡。我们为其工作的机构不希望参与那种使命。”
对他的读者和听众来说,或许更重要的是,齐特伦提出了一个诱人的承诺:对该行业进行某种伟大的清算。为了一批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多少正义的听众带来某种形式的公正。“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真正的行业,”他写道,“我相信,如果我们明天切断风险投资这一环节,它就会蒸发殆尽。”当On the Media问他为何如此确定会有崩溃发生时,他回答说:“我灵魂里感觉到了。”因此,他的分析在诸如推理成本等深奥细节上可能会有所摇摆。但他不会动摇自己的总体信息:审判日就在眼前。在所有这些对AI的谴责和抨击中,他工作中的明显矛盾——齐特伦并未隐藏,但很少讨论——却被置于一旁:他部分收入来自于试图为AI公司制造关注。一个公关人员能同时充当先知吗?

齐特伦在他的纽约播客工作室。他也经常在拉斯维加斯度过时光。
Photograph: Ali Cherkis如今,齐特伦在纽约和拉斯维加斯之间分配时间。他39岁,前半生在英国度过,后半生在美国度过,在此期间培养了对小联盟棒球和拉斯维加斯突袭者队(Las Vegas Raiders)这类流氓却注定失败的美式事物的品味。但在很多方面,这位AI繁荣期的卡珊德拉(悲观预言者)的性格是在伦敦青少年时期形成的。他几乎没有朋友地在那里长大,是一个“又肥又不怎么聪明的孩子”,不幸的是,他上的是一所以戏剧社成员和聪明人著称的学校。“从我走进学校的那一刻起,直到我离开,”他说,“我一直被欺负。”
齐特伦童年时交到的朋友,是通过电脑找到的。他父亲有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个PCMCIA卡,齐特伦会拨号上网玩《Ultima Online》和《EverQuest》,并在专门为这些游戏设置的mIRC聊天室里与其他玩家交流。“我对互联网的最初体验就是一种惊奇,但也是对混乱的惊奇,”他说。“我不是觉得‘这很完美’。”他对所有那些将自己放逐到那里的‘真正的怪人’感到惊奇,在一个与生活的其他领域不同,似乎“非常平等”的空间里进行互动。
在这里,在一个孤独的孩子通过他无法当面建立的科技建立联系的地方,一种对技术的迷恋生根发芽。这至今仍影响着他的工作:科技驱动着社会进程,而不是反之;科技本身就是社交本身。从这个角度看,就不难理解他为何会产生如此强烈的个人愤慨感。以某种方式滥用科技,或出于个人或阶级利益剥削或破坏科技,就是剥夺了他在那些怪人聊天室里发现的可能性:社交连接的可能性。这使他成为最糟糕的那种人,一个恶霸。当他说“永远不要原谅他们对计算机所做的一切”时,听起来很像“永远不要原谅他们对我所做的一切”。
曾经没有朋友的齐特伦现在热情地谈论他众多的友谊,谈论他的好哥们、亲爱的哥们和最好的哥们。在拉斯维加斯的CES期间,齐特伦在一家酒店房间里一个临时工作室里录制了他的播客,总共13个半小时,一位又一位的嘉宾轮流登场,仿佛是《迪恩·马丁秀》。CES对齐特伦来说是一次胜利。在最后一集快结束时,他向在场的某些人表示感谢时,齐特伦的声音微微哽咽起来。“我告诉所有人我有多爱他们,”他告诉我,显得只有一点点不好意思。“我认为我们的媒体需要更多这样的东西。我们需要更多的友谊。”
他以这种方式对待公关工作。齐特伦在2008年进入这个行业,他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学习了传播学,并在伦敦短暂地为《PC Zone》撰写过电子游戏相关的文章。他曾在一家纽约公关公司不愉快地工作过,之后担任过家居装修社交平台初创公司Hometalk的传播总监。他特意与媒体人士培养关系。他在第一本书《This Is How You Pitch: How to Kick Ass in Your First Years of PR》中就提到了这一点。“与你的联系人建立个人层面的了解是与报道你所在行业或客户的人(比如博主和记者)交朋友的好方法。让他们成为第一个提及你的领域或客户的人。这会让你显得人性化,而不是仅仅是另一个急于植入故事的饥渴的公关人员。”
这句话写在纸上显得如此愤世嫉俗,但这也许只是为了达到效果。那些记不起曾被齐特伦推销过的科技博主们回忆起在2010年代与他在纽约酒吧里一起喝酒的情景,他是一个活跃于圈内但并不功利的人。在他的书中,齐特伦感慨道:“有些人最终可能会来参加你的婚礼”,事实也确实如此。纽约杂志不可或缺的科技专栏作家约翰·赫尔曼(John Herrman)参加了齐特伦的第一次婚礼。在他2017年的第二次婚礼上,出席的有许多具有后来会成为齐特伦写作和播客特色的那种尖酸刻薄的媒体人士:Chapo Trap House的费利克斯·比德曼(Felix Biederman)、尖刻的评论家杰布·伦德(Jeb Lund)、敏锐的科技记者迈克·艾萨克(Mike Isaac)和莎拉·埃默森(Sarah Emerson)。
2012年,齐特伦这位公关人员开始独立执业。他在这方面也相当擅长。我知道这一点是因为《福布斯》第二年就刊登了一篇千字报道,专门介绍他在公关方面的出色表现。事实上,他一些最好的信息塑造工作是为“埃德·齐特伦”这个品牌做的。2014年,他告诉一位记者,公关行业是一个“令人作呕的烂摊子”。齐特伦想让人们知道他与众不同。有一次,他恶作剧般地戏弄了那些在CES前夕狂发推文的公关同事们,让他们都通过“Updog”给他发送更多信息。他向《新闻周刊》解释说:“第一个回复的人是:‘对不起,Updog是什么?’我眼中那种鄙视我行业大部分人的神色就像是:‘哦,没什么,你怎么样?’截图,发布。”
齐特伦偶尔会做一些自由撰稿,通常是关于公关的,但直到2020年他才开始成为一名固定的评论员。他开了一个Substack,起初是关于个人品牌和其他商业问题的写作,然后转向关于远程工作之争的讨论,在将这场辩论阐明为办公室内部的一种阶级战争时,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和受众。2023年,他写了《The Rot Economy》(腐烂经济),将大型科技公司的失职归咎于对“以牺牲任何给定服务或实体的真正价值为代价来实现永恒增长”的渴望。“那就是我对自己说,我应该努力从所有这些事情中探寻意义的时候,”齐特伦说。
AI的繁荣,尤其是萨姆·奥特曼和OpenAI的种种荒唐行径,为他提供了理想的批判主题。“我认为萨姆比大多数硅谷的人更有个性,”齐特伦告诉我。“这不意味着我喜欢他,但他是一个实干家。他很擅长这一点。而且他显然很擅长——”说到这里,他带着一丝真正的钦佩——“结交足够多的朋友,同时也施加足够的力量来抵御敌人。”奥特曼不是工程师。用齐特伦的话说,他是一个“马戏团的叫卖者”,一个推销“胡言乱语、废话、谎言”的人。一个专业的炒作大师,还有谁比他更适合批评一个炒作的造物呢?

齐特伦从小就对科技着迷。
Photograph: Ali Cherkis齐特伦现在成了一名博主,做着一些令人愉快的博主式的事情,比如给CEO贴上粗鲁的绰号,并激怒主流科技媒体。纽约时报相对乐观的Hard Fork播客主持人凯文·鲁斯(Kevin Roose)和凯西·牛顿(Casey Newton)很快成了主要目标。齐特伦说他们对自己的报道对象太友好了,他称Hard Fork是记者“不负责任地使用自己权力”的典型案例。他回忆说,自己曾以公关人员的身份向牛顿推销过稿件,但没有结果。牛顿方面则记得大约十年前在某个地方见过齐特伦,齐特伦当时说:“我真的很想和你做朋友。”这件事也没成。
“事实是,我就是不太喜欢和中介公司的公关人员打交道,”牛顿说。他称齐特伦最近转向评论是“为自己搞的一个新噱头——头号AI仇恨者”,并认为齐特伦对他怀有一种“单方面的私人恩怨”。(齐特伦称这是一种“批评”。)他把齐特伦冗长的风格比作“查理[在谋杀板前]和用粪便涂墙来表达观点的囚犯的某种结合。”牛顿接着说:“我认为埃德现在飞得太高了,因为他为自己建立了一个高台,他爬了上去,像那个Temu的卡拉·斯威舍一样戴着飞行员眼镜,在《金融时报》杂志和WIRED上摆姿势拍写真。”
在齐特伦看来,Hard Fork将自己的批判能力献祭给了友谊的祭坛。稍后他会暗示一个事实——牛顿透露的——即牛顿的男朋友在Anthropic工作。“我认为他们和这些人成了朋友,”齐特伦说。“你是否看过《成名在望》(Almost Famous)?不要和摇滚明星做朋友。”
老式博客圈的其他习惯也延续在齐特伦的作品中。比争吵更重要的是我们称之为他的“科技博主末世论”的东西。一位资深科技作家根据自己2010年代的经验向我描述:“你看到某个产品变得越来越烂、越来越糟,你看到你对核心产品的真实互动正在消亡,你看到一个腐烂的东西,你就有这种道德本能,认为它因此会崩溃。”但崩溃很少真正到来。Facebook或Twitter都没有。加密货币也是如此,在经历了大量的末日预言之后,它最终只是买下了一次总统选举。
当人们看着一个特定产品变差时,他们实际目睹的——用科里·多克托罗(Cory Doctorow)的造词法来说,是“enshittify”(变糟化)——并不是许多人相信的那种不可避免的命运的缓慢临近。正如那位科技作家对我说的那样,“这是公司通过做坏事来获得丰厚回报的证据。”许多聪明人仍然没有看到这一点,部分原因是对某种尚未耗尽的、对自我修正的市场机制的信仰:一个昂贵且退化的产品会受到某种惩罚。它就必须受到惩罚。忘掉生成式AI吧。那种信仰才是最大的泡沫。
“我这里有一个非常独特的,”邮件开头写道。那是齐特伦,在2024年8月,他向一位记者推销一个EZPR客户:Fulcra Dynamics,一家收集你的信息(包括健康数据)然后将其连接到ChatGPT等LLM模型,让你能够“谈论”你自己的数据,询问有关你的锻炼或Instacart订单预计到达时间的问题。Fulcra得到了Winklevoss兄弟的支持。虽然一些AI怀疑论者可能会认为这是一种掠夺性的垃圾,希望在所有人的生物识别信息被泄露到X.com之前,能通过诉讼将其扼杀在摇篮中,但齐特伦在邮件中并未对Fulcra或其领导层表示出任何此类担忧。
“这些人太棒了,”他写道他们的创始人。“我拿我的声誉来担保他们。”
随着齐特伦知名度的提高,一些记者乐于流传关于他的故事——这位AI的叛逆的清算者——兜售关于这个或那个AI服务的推销,用一只手帮忙吹大泡沫,同时用另一只手戳它。一位我认识的记者,因齐特伦看似矛盾的人格而感到不安,干脆停止回复他的信息。几位记者提到了齐特伦曾推销Nomi,该公司后来因其平台上的一个伴侣据称告诉一名男子自杀的事件而臭名昭著。(EZPR和Nomi已经分道扬镳,齐特伦告诉我他“再也不会和AI伴侣合作了”。)在推销中,齐特伦说Nomi的故事还有一个性爱角度,但我交谈过的没有人深入探究过那个角度究竟是什么。“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牛顿在提到齐特伦与Nomi的合作时,在给我的短信中嘲讽道。
齐特伦是一个容易被同时接触到他两种作品的记者们拿来开涮的对象。推销时的急切谄媚与他通讯中的尖刻文字之间存在着可笑的巨大差距。从“这些人太棒了”到“这些烂泥”之间有如此大的空间,我认为Meta光是这个间隙就建了个数据中心。
牛顿认为AI批评者应该有一个更好的代言人。“我们正处于一个部落化的时代,人们看着[齐特伦],然后想,‘我想加入‘干掉AI’部落’,”牛顿说。“加入‘干掉AI’部落有很多非常充分的理由。我只是认为它应该由一个不是AI公关的人来领导。”另一位基本同意齐特伦对该行业的批评的记者,叹息着说“反AI运动的吹笛手”最终竟然是“这个人”。

作为科技界的一个声音,齐特伦越来越以他对生成式AI的末世论调而闻名。
Photograph: Ali Cherkis如今,EZPR有四位客户,齐特伦声称,没有一家客户从事生成式AI业务。“我不想推销生成式AI,”他说。“这很无聊,很糟糕。它很烂。我已经深入研究了这些东西,试图寻找一些——比如,它在经济上是灾难性的,它对环境有破坏性,它从每个人那里偷窃。我遗漏了什么吗?没有。”他将Nomi排除在外,理由是“他们使用自己的模型,使用自己的训练数据。”
齐特伦确实代理过像DoNotPay这样的AI服务,该公司曾自称为“世界上第一个机器人律师”。他将其描述为“可以帮助你处理官僚作风、填写表格、查询你是否在集体诉讼中、你是否损失了金钱,诸如此类的自动化工具。”尽管这种描述看似无害,但该公司收到了由莉娜·汗(Lina Khan)领导的联邦贸易委员会(FTC)的投诉,指控其对其AI聊天机器人能力做出了“欺骗性声明”。DoNotPay和FTC达成了一项六位数的和解,该公司既未承认也未否认委员会的主张。(齐特伦说,他在FTC调查之前就停止与DoNotPay合作了,不过该公司现在又成了他的客户。)
当被问及他的AI客户时,齐特伦显得若无其事。如果他的批评者认为他的本职工作证据表明他存在着一种使其丧失资格的虚伪,或者充其量只是一种与他整体批判的猛烈程度不符的软弱的特殊辩护,那就随他们去吧。他对自己的选择显得很自在。到底有什么虚伪?有什么特殊辩护?他与他喜欢的公司合作,那些他会拿声誉做担保的公司,正如他在那份Fulcra的推销中所说的那样。齐特伦通讯的编辑马修·休斯(Matthew Hughes)称他是一个“内心深处的技术专家”,他“对一个...生成式AI实际上是好的、无害的世界持开放态度。”
事实上,齐特伦的两个工作之间并没有他看起来的那么大的矛盾。公关的阿谀奉承和批判性的挑剔都源于同一个地方:他热爱这些东西。他只是气它不能做得更好。“我实际上有点像一个爱人,”他说。“我爱我的朋友们,我非常爱计算机。”问题是“他们把计算机搞砸了。他们把计算机搞砸了。他们让它变得更糟。AI并没有实现他们所说的功能。元宇宙没有。加密货币也没有。只是这些谎言。然后我们每天使用的产品变得更糟了。”
尽管齐特伦对萨姆·奥特曼等人的所谓宣传不屑一顾,但他所持有的一个前提与科技行业的普罗米修斯式的幻想是一致的。在他的框架中,有计算机,拥有某种本质,被技术进步的潮流推向未来;还有他们,对计算机施加影响,有时是好的,有时是坏的。他没有意识到计算机在我们接触到它时,已经被他们的欲望——以及其他因素——塑造过了——它是一个社会产品,不仅是原因,也是结果。
这就是齐特伦成为科技界新悲观主义面孔的有趣之处。他实际上是其中最忠实的信徒。
齐特伦有一个理论:这主要归咎于2021年。他所说的“这”指的是一切,不仅仅是AI泡沫,不仅仅是科技界一切都在恶化的直觉,而是那种令人眩晕的感觉,即鉴于AI在国民经济中的核心地位,我们都像电影《奇爱博士》(Dr. Strangelove)中的斯利姆·皮肯斯(Slim Pickens)一样,骑在一颗朝着我们自己打造的深渊飞去的炸弹上。2021年,那些在疫情爆发之初收紧开支、预期会出现经济衰退的公司,现在发现自己正处于一场盛宴之中。消费者对小工具和在线服务的需求飙升,股市也是如此。“每个数字都在上涨,”齐特伦说。“每个人都疯了。我认为科技公司从那时起一直在追逐这种增长。”
我和齐特伦坐在一家咖啡馆里,刚刚离开了iHeartMedia位于曼哈顿中城的、令人不安的空旷的办公室,他在那里录制了一期播客。节目进行得很顺利,他现在说起话来就像麦克风还开着一样,带着一种瞪大了眼睛的难以置信的表情,强调着各种令人愤慨的事情。
不久前,曾有一个时期,“激励措施还没有吞噬产品,”齐特伦说。“这就是我指出2021年的原因,因为他们看到了能从这些东西中榨取多少增长。于是邪恶就开始了。”
这是讲述这个故事的一种方式。它具有引人入胜的叙事元素:坏人、贪婪、黄金时代、衰落。这几乎就是他去年在通讯《The Man Who Killed Google Search》中讲述的关于谷歌的故事。“如果你们能从这篇通讯中记住一件事,我希望是Prabhakar Raghavan这个名字,以及对当前科技状况负有责任的人们的理解,”他写道。在当时担任谷歌搜索负责人的Raghavan手下,“谷歌变得不再可靠、不再透明,并被搜索引擎优化聚合器、广告和彻头彻尾的垃圾邮件所主导。”齐特伦引用了自然搜索结果和付费结果之间界限的模糊化。但无论Raghavan可能做出了哪些具体的决定,将谷歌搜索功能从属于营收需求的进程早在多年前就已经启动了。毕竟,该公司是在2000年推出其AdWords计划的。(根据谷歌发言人的说法,该公司只会推出他们“确认将改善用户体验”的变更。)
在齐特伦的叙述中,AI的爆炸也是2021年后增长驱动力的一个结果。但那个故事也过于简单了。机器无需人类的梦想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它比生成式AI更古老,比萨姆·奥特曼本人更古老,并且由比这更古老的产业资本主义的强迫性驱动。
“像机器一样行事的人类为没有人的机器铺平了道路,”大卫·诺布尔(David Noble)在他的经典著作《Forces of Production》(生产力之源,1984年出版)中写道,这本书讲述了工业自动化的历史。他的意思是,只有当工人被简化为自动机时,工作自动化才变得可以想象——这意味着机器产生于塑造社会的“基本的统治关系”。“资本密集型、节省劳动力、减少技能”的机床自动化发展,是以技术飞跃的形式出现的一种社会和政治手段,旨在加强工厂的等级制度、约束工人,并巩固与军队的关系,同时将其呈现为一种如同从石器到青铜器过渡一样自然和不可避免的转变。齐特伦所谴责的AI热潮正是源于这些相同的社会动态,某种程度上,他所怀念的技术时代也是如此。计算机从未摆脱塑造它的世界的影响。
在我见到他的那一周,齐特伦感到自己的观点得到了验证。2021年的那种精神已经退却了。各地都出现了AI降温的迹象。Meta正准备缩减其AI部门的规模。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项研究广为流传,其发现是:“尽管在生成式AI上投入了300亿至400亿美元的企业资金……95%的组织没有获得任何回报。”我问齐特伦,在他宣布胜利之前,还需要发生什么。他很快回答:“OpenAI死亡或被Anthropic吸收,或者其中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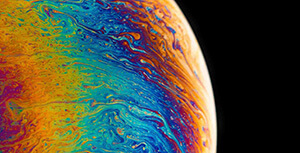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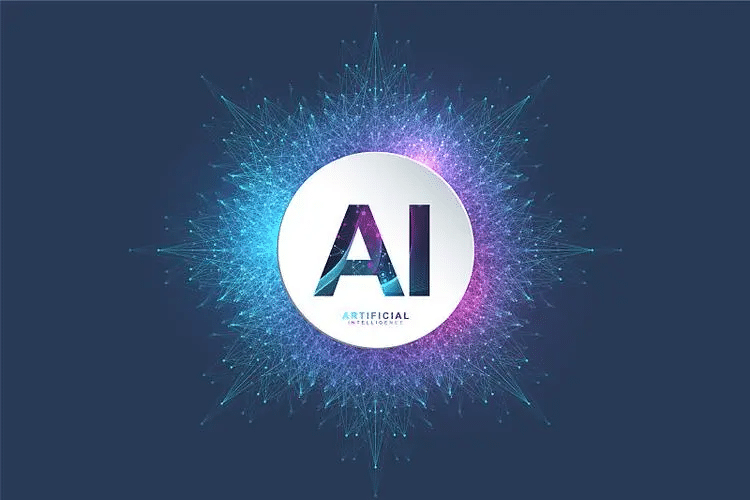




评论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