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载信息
原文链接:https://www.wired.com/story/the-real-stakes-real-story-peter-thiels-antichrist-obsession/
原文作者:Laura Bullard (Wired)
彼得·蒂尔的末日巡演:从哲学辩论到对敌基督的痴迷
彼得·蒂尔的“世界末日”演讲之旅,至今尚未结束。这位亿万富翁已经巡演了整整两年,通过一系列或令人困惑的采访,传播着他关于末日的、带有《圣经》色彩的观点。他与经济学播客主泰勒·科文(Tyler Cowen)讨论了“katechon”(圣经中“阻止者”的术语,指阻止末日降临的力量);与《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罗斯·多瑟斯(Ross Douthat)进行了一些非常尴尬的现场沉默对话;目前,他正在旧金山进行一场关于“敌基督”(Antichrist)的四场非公开系列讲座。
对于不同的人来说,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之一沉迷于布道和恐怖电影中的形象,可能听起来很滑稽、很有趣、令人无法忍受,或是令人恐惧。但要理解蒂尔如何看待自己在政治、技术乃至人类命运中的巨大角色,关键在于探究支撑这些演讲的思想和影响。要真正理解蒂尔的“阻止者”与“敌基督”的把戏,我们需要回顾他末日巡演的第一场主要演讲——那是在2023年巴黎一个异常炎热的日子里举行的。
该活动没有录像,也没有记者报道,但我通过与在场人士的交谈,得以重建当时的情景。
活动地点是每年一度的勒内·吉拉尔(René Girard)学者会议。(蒂尔自称是“坚定的吉拉尔信徒”。)在这次未公开的演讲的晚上,数十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吉拉尔哲学家和神学家聚集在巴黎天主教大学一间朴素的演讲厅里。在讲台上,蒂尔发表了近一个小时的演讲,阐述了他对“末日”(Armageddon)的看法——以及他认为“不足以”阻止这一切的各种因素。
.jpg)
在蒂尔看来,现代世界对自己所掌握的技术感到恐惧,恐惧得太过分了。他指出,我们这个“无精打采”、“僵尸化”的时代,其特点是日益增长的创新敌意、生育率暴跌、瑜伽过度,以及被“全球网络的无尽《土拨鼠之日》”所困扰。然而,在对技术末日——核战争、环境灾难、失控AI等真正威胁——的神经质绝望中,现代文明变得容易受到更危险事物的影响:敌基督。
根据某些基督教传统,敌基督是一个在将人类引向末日之前将其统一于一个统治之下的人物。对蒂尔来说,敌基督的邪恶几乎等同于任何试图统一世界的企图。“这样的敌基督如何才能掌权?”蒂尔问道,“通过利用我们对技术的恐惧,并用敌基督的口号:‘和平与安全’来诱惑我们走向堕落。”换句话说:它会以承诺拯救人类免于世界末日来束缚一个被恐惧困扰的物种。
为了说明这一点,蒂尔暗示敌基督可能以哲学家尼克·博斯特罗姆(Nick Bostrom)等人的形式出现——这位AI末日论者在2019年发表了一篇论文,提议建立一个紧急的全球治理系统、预测性警务和技术限制。但蒂尔看到的潜在敌基督者不止博斯特罗姆一人。他看到了整个时代精神中的人物和机构,他们“一心一意地、不惜一切代价地专注于拯救我们脱离进步”。
因此,人类陷入了双重困境:它必须同时避免技术灾难和敌基督的统治。但对讲台上的这位亿万富翁来说,后者更可怕。基于吉拉尔的理论,蒂尔认为,这种政权只能在几十年病态、压抑的能量之后,引发一场全面爆发的、毁灭文明的暴力冲突。而他不能确定任何“阻止者”是否能抵御它。
哲学家的对峙:沃尔夫冈·帕拉弗尔的介入
蒂尔演讲结束后,一位主持人以委婉的方式指出,这次演讲气氛非常低沉。如果世界正朝着世界末日的危机飞速发展,他问,这位亿万富翁建议我们做些什么?
蒂尔的回答是:击退敌基督。但他补充说,就像吉拉尔一样,他并不擅长提供实用的建议。
几分钟后,一位听众站起来提出了一个修正。“你说的关于吉拉尔的话不完全正确,”一个男声响起。
蒂尔——他经常倾向于强硬地驳倒或压倒他的对话者——眯起眼睛看着说话人,试图确定是谁在反驳。那个声音带着明显的奥地利口音特有的圆润元音和柔和的R音,传达出一种安静而熟悉的权威感。“吉拉尔在很多场合,”那人继续说道,“年轻人都问他:‘我们该怎么办?’而吉拉尔告诉他们:去教堂。”
蒂尔终于似乎认出了说话人。他凑近麦克风:“沃尔夫冈?”
这个声音属于沃尔夫冈·帕拉弗尔(Wolfgang Palaver),一位来自奥地利因斯布鲁克的64岁神学家,蒂尔上次见到他是2016年,当时他们两人都曾在吉拉尔的葬礼上致悼词。帕拉弗尔有着圆圆的脸庞、花白的图书管理员式的小胡子,眼角因笑纹而常年紧缩。但那天晚上在巴黎,他的声音里没有一丝幽默。他显然赢得了这位亿万富翁的尊重。
六个月后,蒂尔在美利坚天主教大学再次发表了他的末日演讲。根据一位与会者发布的回顾,蒂尔的论点基本相同。但这次蒂尔告诉听众,他们个人如何在末日与敌基督之间狭窄的道路上前行:“去教堂。”
在霍夫研究中心(Hoover Institution)的一次十月采访中,蒂尔再次强调了这一点:“吉拉尔总是说你只需要去教堂,我试着去教堂。”今年春天,在播客主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多次试图插话未果时,蒂尔打断了他:“吉拉尔的答案仍然会是类似:你应该去教堂。”
这不仅仅是这一句话。尽管蒂尔从未公开承认沃尔夫冈·帕拉弗尔,但这位奥地利神学家的影响可以说贯穿了蒂尔所有关于敌基督和“阻止者”的言论和著作。在20世纪90年代,帕拉弗尔写了一系列关于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的论文——这位被纳粹征召来为德国从民主转向独裁辩护的德国法学理论家。帕拉弗尔的论文批评了施米特一个不太为人所知、带有神学和末世论色彩的观点——这似乎从1996年两人初次会面起就一直吸引着蒂尔。在蒂尔最近的末日演讲和采访中,他的措辞常常直接呼应帕拉弗尔的研究,有时甚至是逐句模仿。(蒂尔未回应《连线》的置评请求。)

卡尔·施米特
当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亿万富翁之一——这位投资了Facebook和AI革命的金融导火索,共同创立了PayPal和Palantir,并推出了美国副总统职业生涯的人——开始将公开露面的主要精力放在一套大量借鉴纳粹法学家观点的末日理论上时,你才会意识到时代是多么怪异。(比如施米特是第一个公开为希特勒的“长刀之夜”辩护的人。)
但对帕拉弗尔来说,时代更加怪异。他一生都是和平活动家,他最初撰写施米特末世论的理论,是希望将其彻底否定。然而,多年来,帕拉弗尔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对施米特进行吉拉尔式批判的观点,似乎成了蒂尔演讲巡演的路线图,以及蒂尔在世界政治中的大量战略干预的基础——从他对军事技术的投资,到他塑造JD·万斯(JD Vance)和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职业生涯的作用,再到他对“国家保守主义”运动的支持。如果蒂尔认真对待自己的思想,他似乎将这些举动视为对人类历史终结的干预。
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两人一直保持着定期联系,一次在蒂尔的家中会面,并通过短信和电子邮件进行辩论。八月份,帕拉弗尔甚至在因斯布鲁克大学接待了蒂尔,进行了一场为期两天的闭门“彩排”,即蒂尔四场旧金山敌基督系列讲座的预演。在接受奥地利新闻媒体《Falter》的采访时,帕拉弗尔表示,他同意这次活动是“希望蒂尔能重新考虑他的立场”。在我与帕拉弗尔交谈的几个月里,他表示担心这位投资者对施米特的看法可能导致了灾难性的解释。
而且,你可能不会相信,帕拉弗尔和蒂尔的关系性质变得更加复杂。帕拉弗尔一直不愿公开反对蒂尔,在我们的谈话中,他有时会淡化自己对这位亿万富翁的影响力和分歧。也许是因为,作为吉拉尔的追随者,他们都相信任何两个反对者(如帕拉弗尔反对施米特,蒂尔反对敌基督)如果反对得足够强烈,就必然会模仿对方并被卷入其中。正如蒂尔自己所说:“也许你谈论末日谈得太多,实际上是在秘密推动敌基督的议程。”
亦敌亦友:两位奥地利人的不同路径
在某些方面,帕拉弗尔和蒂尔一直是一对镜像。
帕拉弗尔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的一个小镇长大,离德国边境不到一小时的路程。他童年的风景是田园诗般的:连绵起伏的山谷和田野,点缀着小教堂,被高耸的白雪覆盖的山脉环绕。但历史背景则不那么平静。帕拉弗尔出生于二战盟军在奥地利投下最后一枚炸弹的13年后,在他四岁生日后的一个月,古巴导弹危机将世界推向了核战争的边缘。
从年轻时起,帕拉弗尔就是和平活动家,18岁时登记为良心拒服兵役者,在大学时组织反对核武器的活动。正是在一门关于人类暴力根源的课程中,他开始研究勒内·吉拉尔的作品——吉拉尔不寻常的理论在欧洲部分地区引起了轰动。
帕拉弗尔了解到,吉拉尔的核心见解是,所有人类都是模仿者,从他们的欲望开始。“一旦他们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人类就会强烈地渴望,”吉拉尔写道,“但他们不确切知道自己在渴望什么。”于是人们模仿他们最受尊敬的邻居的愿望——“从而确保自己与那些他们同时憎恨和钦佩的人之间,生活在永恒的冲突和竞争之中。”
根据吉拉尔的观点,这种“摹仿”(mimesis)——这种无休止的复制——在人际关系中不断反弹和积累。在群体中,每个人都开始变得相似,因为他们都趋同于少数几个榜样,模仿相同的欲望,并为相同的目标激烈竞争。这种“摹仿性竞争”之所以没有立即爆发成全面战争,只是因为到某个时刻,它往往会集中爆发成“众人反对一人”的战争。通过吉拉尔所说的“替罪羊机制”,每个人都团结起来反对一个不幸的目标,并将群体所有的弊病归咎于此人。这种机制对文化凝聚力至关重要,吉拉尔写道,替罪羊叙事是所有原始文化的奠基神话。
但吉拉尔认为,基督教的到来标志着人类意识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它最终揭示了替罪羊是无辜的,而暴民是堕落的。在受难叙事中,耶稣被集体暴力残忍地杀害。但与几乎所有其他牺牲神话不同,这个故事是从替罪羊的角度讲述的,观众情不自禁地理解了其中的不公。
随着这一顿悟,吉拉尔写道,旧的替罪羊仪式立即开始失去效力,因为它们已被揭露和名誉扫地。人类不再能从集体暴力行为中获得相同的解脱。社区仍然时常会树立替罪羊,但所获得的团结凝聚力却越来越少。那么,在历史的尽头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呢?是失控的、具有传染性的、并最终导致世界末日的摹仿性竞争的暴力。
然而,受难叙事的积极方面在于,它为人类提供了道德救赎。对吉拉尔来说,结论很明确:无论结局如何,都必须完全拒绝替罪羊行为。模仿仍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的榜样。他认为,前进的正确道路是模仿耶稣——那个永远不会成为“迷人的竞争对手”的榜样——过一种基督教非暴力生活。
吉拉尔的理论几乎立刻成为了年轻的帕拉弗尔的指路明灯,他认识到这是他和平活动主义和神学之间的桥梁。“你发现了吉拉尔,”帕拉弗尔说,“你就拥有了一个批评所有替罪羊者的完美工具。”而这位年轻的活动家已经将某些主要的替罪羊者锁定在目标之中。
1983年——与他学习吉拉尔的第一堂课是同一年——因斯布鲁克的(天主教)主教试图阻止帕拉弗尔召集一群年轻天主教徒加入当时规模最大的反美导弹示威活动。主教认为帕拉弗尔的观点是地缘政治上的幼稚,让他去读一本名为《兄弟情谊的幻觉:拥有敌人的必要性》的德语文章集。帕拉弗尔意识到,这本书充满了对卡尔·施米特思想的引用——施米特认为政治以区分朋友和敌人为基础。读完这本书,帕拉弗尔发现自己“几乎对每一个句子都持反对态度。”
因此,作为一名博士生,这位奥地利青年决定撰写一篇基于吉拉尔理论对施米特的批判。他将运用吉拉尔的理论来反驳一位欧洲上一次大灾难的法律设计者,这位设计者当时正在激励着挑起下一次冷战的人们。“关注施米特,”他解释说,“对我来说,意味着要反抗我和平主义态度的头号敌人。”
到20世纪80年代末,帕拉弗尔已成为因斯布鲁克大学教职人员中一小批吉拉尔追随者之一。吉拉尔的思想在欧洲其他学术圈也日益流行。但吉拉尔本人继续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发展他的理论,相对低调。
斯坦福的交集:从反体制到“押注摹仿”
当蒂尔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抵达斯坦福时,他是一个带着里根时代反共热情的少年自由意志主义者,对他在南非专制寄宿学校的经历深恶痛绝,并怀有一种他自己所描述的、赢得“一场又一场竞争”的冲动。他很快就扮演了典型的过度成功的保守派校园刺头角色。他加入了斯坦福国际象棋队,保持着优异的成绩,并且是《斯坦福评论》(The Stanford Review)的创始编辑——这是一个右翼学生出版物,在当时大规模学生示威活动抨击西方经典和南非种族隔离之际,它对多元化和多元文化主义的时髦政治大加嘲讽。
因此,蒂尔被罗伯特·哈默顿-凯利(Robert Hamerton-Kelly)所吸引并不奇怪。这位脾气暴躁、神学保守的斯坦福校园牧师曾自称是“一个带着法西斯寄宿学校教育的南非乡巴佬”。哈默顿-凯利教授西方文明课程,据校报报道,他曾至少有一次遭到校园内反种族隔离听众的喝倒彩。根据认识他们两人的几位人士的说法,蒂尔开始将哈默顿-凯利视为导师。正是通过他,蒂尔才得以与吉拉尔本人相识。
哈默顿-凯利是吉拉尔在斯坦福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也是摹仿理论在美国最响亮的倡导者之一。他还负责在校园的一个拖车房里组织一个双周吉拉尔研究小组,应他的邀请,蒂尔在20世纪90年代初成为那里的常客。蒂尔自己承认,他最初被吉拉尔的摹仿思想所吸引,纯粹是因为这与时代精神相悖。“这与当时的潮流格格不入,”蒂尔在2009年的一次采访中说,“所以它对一个有点叛逆的本科生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除此之外,蒂尔对摹仿理论的第一印象是它“太疯狂了”。
但蒂尔在某个时刻意识到——与安·兰德(Ayn Rand)幻想的少数英雄式、自主决定的个人对抗一群苍白的遵从者不同——没有人能免受模仿性欲望及其挫折的影响。从斯坦福法学院毕业后,蒂尔在一家享有盛誉的华尔街公司获得了一份令人垂涎的证券律师工作——几乎立刻就讨厌上了。“从外面看,这是一个每个人都想进去的地方,”蒂尔后来回忆说。“在里面,这是一个每个人都想出来的地方。”然后,当他申请担任保守派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Anthony Kennedy)和安东宁·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的书记员时,两人都拒绝了他。据他自己描述,吉拉尔的竞争理论正逐渐触动这位高度摹仿的蒂尔。“在我二十多岁经历那场持续的四分之一世纪危机时,”他说,“我对这种激烈的竞争和取胜的欲望产生了质疑。”
最后,在瑞士信贷集团(Credit Suisse Group)短暂担任衍生品交易员之后,蒂尔返回湾区,开启了使他成名的科技生涯。但在回到加州的同时,蒂尔也回到了吉拉尔身边。1996年夏天,28岁的蒂尔参加了吉拉尔信徒的年度会议,那年会议在斯坦福举行。在活动的最后一天,他在一个演讲厅里找了个座位。当时从未谋面的沃尔夫冈·帕拉弗尔正准备向英语听众介绍他对卡尔·施米特关于敌基督和“阻止者”理论的首次英文批判。这次演讲将为蒂尔未来30年的思想设定一个新的方向。
施米特的“阻止者”与纳粹的失败
作为理论家,施米特最出名的是两件事:他对魏玛时期自由主义的深刻批判,以及他在二战前夕加入纳粹党(但在1936年被帝国抛弃)的决定。帕拉弗尔告诉他的听众,施米特对纳粹的拥护源于他对一个“全球国家”下“撒旦般的统一世界”的恐惧,施米特将此等同于敌基督的统治。
根据帕拉弗尔的说法,在二战期间,施米特认为苏联的全球主义野心正是构成了这种末日风险。施米特迫切希望找到一个“阻止者”——即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中提到的神秘人物,他在敌基督到来之前阻止它,从而推迟世界末日。帕拉弗尔说,施米特“最大的失败”是“认为希特勒是一个能够阻止一个毁灭性世界国家到来的阻止者”。
根据吉拉尔的摹仿理论,施米特试图解决一个无法解决的政治问题。施米特对希特勒的支持实际上是对替罪羊机制音量调高的赌注——即德国可以通过将所有愤怒引向犹太人、罗姆人、外国势力以及纳粹指定的其他对帝国有害的敌人来实现社会稳定。但帕拉弗尔说,施米特的“阻止者”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
“施米特太晚才意识到,他对希特勒的支持实际上是在为敌基督服务,”帕拉弗尔告诉吉拉尔信徒们。施米特警告“一个统一世界的极权主义危险”是正确的,但旧的替罪羊仪式已不再可持续。施米特依靠一种残酷的民族主义理念,将本国人民视为朋友,将其他所有人视为邪恶的敌人。吉拉尔证明了世界正在超越这种方案的可行性。因此,施米特的计划最终适得其反。纳粹党的暴行是如此令人发指,以至于它们促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全球性机构的自发形成。大屠杀为联合国铺平了道路。他的“阻止者”原来是一个敌基督。
这就是吉拉尔的困境。如果控制暴力的旧结构不再起作用,一个暴力的、终结世界的末日似乎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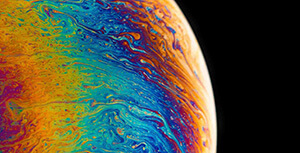

评论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