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4年初,Anthropic、Google、Meta和OpenAI等公司曾一致反对将其AI工具用于军事目的。但在接下来的12个月里,情况发生了变化。
1月,OpenAI悄悄撤销了对其AI工具用于“军事和战争”目的的禁令,随后有报道称该公司正在与五角大楼合作进行“多个项目”。11月,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成功连任的同一周,Meta宣布美国及其部分盟友将能够为国防用途采用Llama模型。几天后,Anthropic宣布也将允许军方使用其模型,并表示正在与国防公司Palantir合作。随着年底的临近,OpenAI宣布与国防初创公司Anduril建立合作关系。最后,在2025年2月,谷歌修改了其AI原则,允许开发和使用可能伤害人类的武器和技术。在短短一年内,对AGI(通用人工智能)生存风险的担忧几乎消失了,AI的军事用途也变得正常化了。
部分转变与构建这些模型所涉及的巨大成本有关。对通用技术的(其他GPTs)研究通常强调国防部门在克服采用问题方面的重要性。经济学家David J. Teece在2018年写道:“当存在一个规模庞大、要求苛刻且能创收的应用部门时,GPT的发展会更快,例如美国国防部对早期晶体管和微处理器的采购。”国防合同的软预算限制和长期性质,加上往往模糊的成功指标,使得军方成为新技术的理想客户。特别是考虑到AI初创公司需要确保大量且耐心的投资,转向军事融资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能解释转变的速度,也不能解释所有领先的美国AI研究实验室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的这一事实。
过去几年极大地改变了资本主义竞争的格局——从一个由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理念指导的竞争,转变为一个被地缘政治担忧所充斥的竞争。要理解从新自由主义到地缘政治的转变,就必须领会国家与大型科技公司之间的关系。这种国家-资本关系是早期帝国主义形成的核心要素——列宁将他那个时代的帝国主义描述为垄断资本与大国之间的融合——并且在20世纪一直具有影响力。近几十年来,这种关系表现为科技精英和政治精英之间就数字技术在创新、增长和国家权力中的作用达成了广泛共识。
然而,近年来,精英群体之间的这种利益和谐已经瓦解。一系列重叠的过程,特别是在2010年代获得了巨大动力,瓦解了这一秩序,在美国和中国都留下了潜在新格局的碎片。
硅谷共识
直到2010年代中期左右,美国一直由所谓的硅谷共识主导。在这种共识下,政治精英和科技精英在技术在世界上的作用、允许技术蓬勃发展所需条件、它们所体现的所谓美国价值观,以及技术部门资本积累的要求等方面达成了广泛一致。对于科技精英和政治建制派而言,全球化的通信、资本、数据和技术都服务于他们的利益。
硅谷共识之所以吸引科技精英和政治精英,是因为它相信技术有能力创造一个由美国主导的、无国界的商业和数据世界。虽然科技部门(最初)可能比国家务实的政治现实主义更具乌托邦色彩,但双方都看到了通过相同手段可以实现其共同目标。
在实践中,这意味着科技部门获得了自由裁量权,监管要么明显缺失,要么奇特地起到了促进作用。放松管制当然是更广泛的新自由主义时期的核心要素,但它尤其适用于那些有能力混淆现有监管类别并“颠覆”现有规则的技术公司。缺乏任何重大的联邦隐私法或对零工经济中工人地位的行动,都表明了这种允许数字公司随心所欲行事的广泛意愿。在比尔·克林顿总统任内,全球电子商务框架制定了政策,据国际研究教授Henry Farrell所言,这些政策“成功地‘劝阻了政策制定者对数字经济征税或进行监管’”——转而依靠行业主导的自愿监管。这里的核心信念——至今仍然有效——是任何监管都只会阻碍创新和美国技术与力量的扩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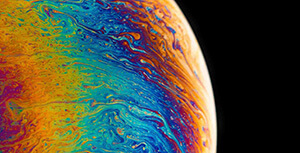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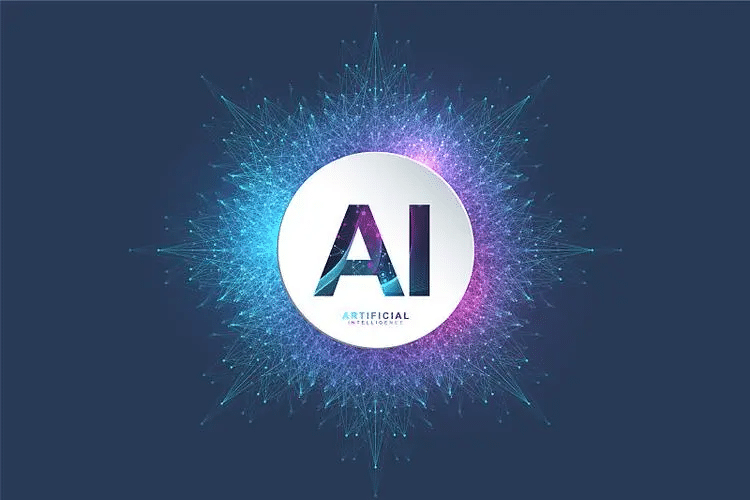


评论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