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载信息
原文链接:https://www.wired.com/story/the-big-interview-podcast-jonathan-nolan-fallout/
原文作者:Katie Drummond
乔纳森·诺兰(Jonathan Nolan)早就预见到了这一切。作为编剧,他曾参与他兄弟克里斯托弗·诺兰(Christopher Nolan)的许多电影,从《星际穿越》到《黑暗骑士》系列。与妻子丽莎·乔伊(Lisa Joy)合作,他创作了HBO的《西部世界》,并担任了亚马逊Prime剧集《辐射》的执行制片人。但在那之前,他在电视领域崭露头角是创作了CBS的《疑犯追踪》,这是一部关于一位孤僻的科技亿万富翁,他创建了一款旨在阻止犯罪在发生前就将其破获的监控软件。虽然那是虚构的,但很难不觉得它具有先见之明。
随着《辐射》进入第二季,诺兰也关注着未来。该剧改编自同名电子游戏系列,讲述了一个后末日时代的美国,每个人都必须以任何方式生存下来。这部剧集极其有趣,充满了20世纪50年代的复古未来主义风格。
那么,诺兰在未来几十年里看到了什么?很多。首先,他不认为人工智能会取代人类电影制作人。事实上,他认为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有抱负的导演入门。(尽管他说自己永远不会在写作中使用它。)他还希望看到(大部分)社交媒体的消亡——但他也明白这可能永远不会发生。
对于本周的《大咖访谈》(The Big Interview)播客节目,我向诺兰询问了所有这些以及更多内容。下面是关于他撰写蝙蝠侠电影、经典汽车以及他会带进自己末日地堡的物品的看法。
本次访谈已为篇幅和清晰度进行了编辑。
凯蒂·德拉蒙德(KATIE DRUMMOND):乔纳森·诺兰,欢迎来到《大咖访谈》。
乔纳森·诺兰(JONATHAN NOLAN): 谢谢你的邀请。
我很高兴能在纽约见到你本人。这里非常冷。我来自加拿大,所以我的衡量标准有点偏差,但是……
我来自芝加哥。我倾向于认为纽约的冷算不上是真冷。
不,不,这很真实。我年纪越大,就越虚弱、越孱弱。所以我受不了[这种冷]。
我已经在洛杉矶待了25年了。完全不行了。
所以我们俩都完全不行了。这将是一次很棒的对话。我们总是喜欢用一些快速问答作为热身。实际上,这对今天可能会有帮助。但这只是为你大脑做准备的快速提问。你准备好了吗?
我之所以成为一名作家,就是因为我不擅长快速回答问题。所以我肯定会搞砸的。
哦,太好了。那我们将用掉整个小时。
就是这样。
科幻小说中最被滥用的桥段是什么?
哦!超光速旅行。
为什么?
因为它是一种叙事上的便利,我想我们在《星际穿越》中用过它,但我们是以一种略带迂回的方式使用的,那就是虫洞。这感觉不太一样,但效果是一样的。这只是跳过无聊部分的手段。
你反复阅读的一本书是哪一本?
最近,我一直在重读伊恩·班克斯(Iain Banks)的《文明》(Culture)系列的所有作品。多年前,我一直在寻找科幻小说中对人工智能的积极描绘。
哦,有意思。我们等下要聊这个。
几乎没有,真的没有。一边是詹姆斯·卡梅隆(James Cameron)式的描写,另一边是虚无。伊恩·班克斯在20年间写了这些书,从80年代末开始,直到2010年代初去世,太早了。但它们是对人类和人工智能融合文明最充分、最精彩的描绘,他们似乎已经解决了问题。
你手机上现在最奇怪的App是什么?
最吸引我注意力、而且很糟糕的App是一款叫做“Bring a Trailer”(带个拖车)的。
那是什么?
它是用来购买经典汽车的。我来自芝加哥。11岁时我移民到美国。当我拿到驾照时,我就成了美国人。我再也没有回去过。我一直都很喜欢汽车。
你是个车迷。我的研究里没有提到这个。所以你正在用一个App来看车,看是否要买。
经典老车,这类东西。你知道,我喜欢电动汽车。我已经开电动汽车很多年了。它们很棒。但很明显,我们正处于这个时刻,比如,我想念白垩纪的手机时代,当时有数百万种不同的形状。有翻盖的、滑盖的、做各种事情的。然后iPhone出现了,现在它只是一个单调的、极其实用的[东西]。你知道,形状或功能上没有任何多样性。汽车现在发生的就是这种情况,而且速度快得惊人。就像特朗普还在试图坚持,但你看中国,大门早就敞开了。
所以你在寻找那些古怪的、多样的……
……老式的、内燃机的、手动变速箱的汽车。
哇。好吧。那确实是个奇怪的App。写一个完美的结局和写一个完美的试播集,哪个更难?
完美的试播集。完美的结局更重要。你赋予它们价值,因为如果没有结局,你就一无所有。但事实上,没有结局的开始就像没有笑点的笑话一样。有一天我走进J·J·艾布拉姆斯(J.J. Abrams)的办公室,我们谈论了一段时间的电影,然后我以剧集制作人的身份离开了。我把这段经历比作我的领带被卷进了碎纸机。这就像‘哦,我来做一点这个……’然后,15、16年后,我就在这里了。但是写试播集是一种令人抓狂的经历。作为一个电影编剧,你看着所有那些很酷的东西,你可能不得不删掉一些。但在电视里,就像我有一百件很酷的东西,而我只能给你看四件,我必须选出最合乎战略的最佳组合。没有收尾,这非常困难。
如果你必须被困在一个数字模拟中,你会选择哪一个?
哦,哇。
我们喜欢用这些问题来找点乐子。
你知道,我们都是父母,但能够接触到,老实说,现在的这些年,你的孩子还很小,事事都依赖你。但他们充满了迷人的见解,而且你知道,那种亲密感和贴近感是不可思议的。我兄弟的孩子们年纪大了。我看到了事情的发展。一路走来都很棒。但是你永远不会再有这样的一刻了。
好吧,别让我哭。所以你希望生活在一个你的孩子仍然容忍你的、相对年幼时的现实的数字模拟中。
嗯,别夸张了。我不确定他们是否爱我崇拜我,但他们能容忍我。
你希望生活在一个你的孩子仍然容忍你的数字模拟中。
是的。我接受这个。
这很触动人。我也会的。我很想永远生活在那个世界里。
是啊。呃,肯定。
谷歌搜索还是ChatGPT?
当然是谷歌搜索。
同意。现在,你写了被改编成电影《记忆碎片》的短篇小说。你有没有纹身?纹的是什么?
我和我的嫂子艾玛(Emma),她和我一起制作了那部电影,在制作期间讨论过纹身。然后我们都退缩了。
不,开什么玩笑。
如果你在拍那部电影时没有去纹身,那你永远都不会去纹身了,所以……
永远不会。
我是一张白纸,正如他们所说。
你的创作流程中最“勒德分子”(Luddite,反对技术进步的人)的部分是什么?
我不会把它归类为勒德分子,但我们仍然用胶片拍摄一切。我的意思是,我们稍后可以回到这个话题,因为它与人工智能有关,但数码相机的承诺是它们将节省大量的金钱。我的观点是,这也适用于人工智能,我从事这个行业25年来,我所接触到的任何技术,都没有让我们的电视制作工作变得更便宜过。如果你绘制过去50年胶片或电视的经济图,我敢挑战任何人指出数码相机介入并实现民主化的转折点。因为它从来没有。所以我们用胶片拍摄,因为它成本相同,而且看起来更好。
最后,你的末日地堡里必须有的一样东西是什么?
任天堂Switch。
还有一些游戏,我猜。
是的,肯定。
你有末日地堡吗?
如果你有末日地堡,我认为就像《搏击俱乐部》一样:第一条规则就是不要告诉别人你有末日地堡。我没有地堡。
还没有。
我是技术乐观主义者。
让我问你一个问题:当我准备和你见面时,我回顾了你的职业生涯,看到了《疑犯追踪》。读到有关它的内容真的让我回想起过去。《星际穿越》、《辐射》。我想说,在电影和电视领域,很少有人能像你一样,始终如一、广泛地探讨技术、科学和人工智能。你一直坚持这些主题。是什么让你不断回到这些主题上的?
这是对我说我有点钻牛角尖的一种非常奉承的说法。
得了吧。这是一个很大的领域。
我为我哥哥和大卫·海曼(David Hayman)在华纳兄弟写了一部从未拍成的电影,它与《盗梦空间》和《疑犯追踪》有很大的重叠。我们从未真正地回归过它。但它是关于人工智能的,是关于人工智能作为反派的。
这是2000年代初期吗?
2005年。它没有成功,但我对这个主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做了很多研究;我研究了很多。下一个热门点是《星际穿越》中的机器人角色。我一个项目接着一个项目,心想:“写机器人会不会很有趣?”你知道,像《异形》或几乎所有版本的电影中,机器人船员的张力在于他们最终会反抗并谋杀所有人,他们有一个秘密议程。
但如果他们没有呢?如果他们只是承载了我们认为最美好的所有美德呢?比如他们勇敢、无私、爱讽刺、有趣。优秀的领导者。如果他们始终如一地体现这些价值观呢?也许一开始会让观众感到轻微的不适。然后是一种有趣的“哦,好吧,这是一条出路”的感觉。对吧?剧本并没有规定这条路必须是人类形式的仇外心理。
我也对这样一个想法很着迷:当有如此海量的数据洪流涌现时,会发生什么?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筛选它,找到模式和意义呢?
这证明是非常有先见之明的,我必须说。
抱歉,我漏掉了一点。《黑暗骑士》中有一个关于大规模监控的情节转折。布鲁斯·韦恩(Bruce Wayne)建立了一个在道德上有问题的系统,窃取信息,通过他能同时绘制整个城市的地图的能力,对每个人的手机进行回声定位。那是在权衡我们对保护我们的人的信任程度,政府如何监视我们,以及他们能把这些信息用在什么好地方上。所以,大规模监控被组织起来并过滤成能帮助人们的东西的想法,一直让我很着迷,这也是人工智能的起源点,一个自然的起点。
当我们试图筹备《西部世界》时,显然我们离这个主题最近。安东尼·霍普金斯(Anthony Hopkins)很感兴趣。然后,就像总是发生的那样,制片厂和经纪人之间来回拉锯了很长时间,我们开始觉得我们要失去托尼了。所以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有一句台词,那是我晚上散步时想到的,内容是:“我们曾经活过,在那之前。” 很难界定,但你可以感觉到它,你可以感觉到这个障碍,这个转折点。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折点,而且你感觉它来得非常快。你无法想象像《星际穿越》那样的大浪。你不知道海浪的另一边是什么,但你知道它就要来了。对我来说,那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刻。
所以,我们开始撰写这些电影,并观察系列剧中发生的事情。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故事。所以我的问题是:“我们还能写什么别的呢?”
当你想到写那封信,感觉自己正站在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正站在的悬崖边上时,站在中间的体验对你来说是怎样的?
没有“我早就告诉过你”的痕迹,因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现在也不知道。我认为我们正处于那波浪潮之中,但现在发生的大部分事情,关于推销……现在发生的大部分事情都是炒作。我们在自己的行业中正在应对这种情况。我们对电影和电视中即将来临的事情感到非常恐惧。其中很多都是炒作。我们已经进入了两年,现在我们面临下一次合同谈判,感觉就像,好吧,那些成果带来了多少?它真的改变了我们所做的事情吗?
我想当我们真正坐下来使用这些工具,并思考这些工具的作用时,我几乎完全在两种完全对立的世界观之间撕裂。
一种是,这些工具基本上就是一个被注入了正确经济活动和卓越性的改进版浏览器搜索功能。我从没想象过意识。我不认为人类意识有什么特殊或优越之处。这是我们为《西部世界》花了很多时间思考的东西。
这种信念的另一面是,像LLM这样简单的事物可能会产生一种认知,这种认知将越来越难以与人类认知区分开来。到那时,我们肯定就处于我所看到的那个时刻的中间了。因为人工智能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有过很多次“狼来了”的虚假开端。那些时刻让人感觉“它要来了”,每个人都为此做好了准备,我们进行了很多像这样的对话,然后几年后,它就有点平息了。
在我两分半前刚开始在WIRED的工作时,突然间,每个人都在谈论它。当然,其中很多是这项研究和这些工具中真正引人入胜的进步。然后,如你所说,是营销、炒作和夸大其词。以及商业化。这些公司需要展示投资回报。真的很难理清头绪。当这一切都发展如此之快时,你如何充实自己?
这很艰难。其中一种方式,这不是我们有意为之的,但由于《西部世界》的成功——当时HBO正将自己定位为一家科技公司,以期被收购并与Netflix竞争——所以我们第一次向任何一大群人展示那部试播集时,是[前HBO首席执行官]理查德·普莱普勒(Richard Plepler)在他位于山景城的巨大豪宅里与[投资者]尤里·米尔纳(Yuri Milner)安排的一次活动。我们播出了试播集,然后进行了问答环节。萨姆·奥特曼(Sam Altman)是主持人。他带着他所有的Y Combinator的人在那里观看。
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就受到了关注并被卷入了那群人中;在制作那部剧的过程中,我们与一些领导者走得很近。所以早在15年前,我就听说了DeepMind在被谷歌收购之前发生的事情。那里有一种终止实验的标准,这就直接进入了《西部世界》。奇怪的是,我们无意中成为了过去10到15年发生的大部分事件的前排观众。所以要保持密切关注并倾听。
但即使现在,事态的节奏、强度、基调也在快速变化。我们正处于一个非常泡沫化的时刻。我立刻对此表示怀疑……
是的,我不喜欢泡沫。
这通常意味着一个泡沫破裂或某种障眼法,而不是[真正]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们仍然受邀参加这些对话,与那些走在最前沿的人进行的闭门会议。
所以你仍然与那个行业非常接近。你正在获得一个前排座位。
是的。是的。
这一定非常有趣。
这很迷人。
我知道这些是闭门会议。我假设它们是“不对外记录”的。但这些会议有没有得出什么结论,哪怕是一个想法或让你朝着某个方向倾斜或改变你对这项技术看法的概念?
百分之百有。
我认为我的一个观察,然后与一位领导顶尖公司之一的朋友进行了反复讨论,是我们花了一整天时间与这个团队讨论这些东西能做什么。你知道,它将走向何方?它的应用是什么?因为我认为这是更大的问题之一。
我认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可能会出现像二战中那样,许多技术从战争努力中涌现出来的时刻。你知道,过去40年积累的智慧才达到了这个地步,你不会想要一夜成名,对吧?那位终于拿到奥斯卡、格莱美奖的演员或歌手,可能已经做了20年了。这些神经网络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它不是一夜成名,但正如你所指出的,两年前半,它突然从计算机科学家的一个晦涩的谈资,变成了我们所有孩子日常的事实。每个人。到处都是。
我意识到,与过去一些技术不同,那些技术的应用更清晰,而这个技术更像是外星飞船坠毁在地球表面。这些公司和我们所有人都在探索它的废墟。我们走进一个房间,会说:“哦,该死,我可以进行瞬间移动。” 走进另一个房间,会说:“好的,我可以拍电影了。” 这与其说是我们在创造这些东西,不如说是我们偶然发现了它们,因为我们创造了如此强大和递归的东西,它几乎每周或每月都能喷涌出这些奇迹。
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Veo的视频时,第一次发布时,你就看着它,然后说:“哦,天哪。” 因为我以这个为生。我们花了很多钱来制作看起来效果很好的镜头和特效。
我在游戏界有很多朋友,我知道他们花多少钱来做事情。然后你有一个产品,就像,哦,它是一个10美元的订阅,你可以做这个、这个、那个。 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凡的时刻,与其思考一个应用,然后用几年的时间,动用少数几个高级学位去追逐它,不如说,这里有一个巨大的泥潭,而你将在其中挖掘,并从中找出一些东西,再从那里找一些东西。
抛开炒作,这些技术确实具有变革性。毫无疑问。它们将改变教育和医学,改变所有人都在谈论的所有通常事物。它们将改变文化。我们还没有解决社会后果。别管把精灵放回瓶子里了。我们如何说服精灵不要摧毁经济的整个部分?
谁能告诉精灵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敢肯定这在你的行业中是重中之重,但更广泛地说也是如此。你是一个家长。你在考虑这对你孩子20年后的影响。
或者明年。
确切地说。
这很吓人,也很令人兴奋。当然,其中一些产品让你有很多理由持愤世嫉俗的态度,但我与一些处于这些事情最前沿的人有过几次谈话,他们对这个问题有着非常清晰和引人注目的人文主义观点。
他们会想到那些处于不利地位、无法获得我们孩子可能拥有的东西的孩子。我们在大流行中看到了这一点,对吧?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孩子带到房子后面建了一个小型的学校,并雇了一个老师。我们只是重建了我们能做的事情。
这些工具可以成为一个永远不会忘记你问过的问题的导师。在你睡觉时,帮你研究奖学金。这可能是为那些没有这些优势的孩子提供这些工具的完美方式。它可能真的在为他们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这些工具大多是免费的。所以这个东西的悖论是你说,“谁掌握了这些东西的钥匙?” 我非常——我非常担心这一点。
你去年在《 Semafor》的采访中对人工智能发表的一个有趣评论是关于你如何使用它。他们问你是否使用AI写作,你说:“哦,天哪,不。那是跨越了卢比孔河。”
是的。
你看到它的用途了吗?你是划定了明确的界限,说“绝对不行”吗?你认为人工智能在艺术和创意方面处于什么位置?
我想可以从两种方式来理解这句话,一种是认为这是一种政治立场。完全不是;它更像是一种迷信,对吧?有些作家喜欢写作。有些作家忍受写作。我忍受写作,我觉得写作极其困难。我喜欢写完之后的感觉。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写完东西并感觉自己做到了的那种感觉。
这对你来说是怎样的?
很多时候就是坐着,把头撞在墙上。很多踱步,很多巧克力,很多散步。这就是问题所在,对吧?我以前抽烟。在我写我第一部有报酬的电影,也就是《致命魔术》时,我像上大学时一样抽烟。我意识到,如果我写完那部剧本时还在抽烟,我就永远戒不掉了。因为如果剧本写得好……
我想很多作家,如果你在听这段话,你完全明白他在说什么。
我在写剧本中途成功地一下子戒掉了烟,这样如果剧本写得好,如果它奏效了,我就永远不会指望它说:“我真的得回去抽烟了。” 它会每次都把你拉进去。我对人工智能也是这么想的。这不是对它的价值的评估。我只是觉得,如果我让它进入我本已充满痛苦的创作过程,我就永远找不到出路了。
但它对研究来说非常棒。比如你正在做一个改编或重启之类的事情。你可以深入其中,提出问题。比如,“告诉我书中哪个地方某个角色第一次谈论了他们的童年。” 这是一种加快处理收集信息这种更难方面速度的方法。
有一种美好的想法认为我们会省钱。它从来没有变得更便宜。我与(《辐射》游戏总监)托德·霍华德(Todd Howard)谈过游戏方面的事情。那些游戏就像大制作电影一样。它们变得越来越大。没有什么是能省钱的。数码相机没有让它更便宜。数码后期制作过程没有让它更便宜。
所以你认为人工智能可能淘汰大量工作并降低影视制作成本的想法是站不住脚的谬论?
这完全有可能。几个月前《纽约客》上有一句精彩的引文,大意是,如果公司管理层认为这些工具可以取代所有人,那说明他们太容易上当了。这是因为它被过度炒作了,对吧?它设法在罢工期间吓到了我们所有人。这也是罢工持续这么久的原因之一。如果他们做出错误的决定,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但假设人们每年仍然想要一定数量的大制作电影和一定数量的大制作剧集,这些工具的应用……你知道,我的圈子里有很多担忧、争吵和对话。上帝保佑他们,科技公司会下来进行调解。这就像北加州的代表团下来拜访南加州的代表团。
我的意思是,他们甚至都懒得理会纽约的记者代表了,所以我很高兴听到他们还在和你们交谈。
有时那些会议有点激烈。上次我在其中一次会议上,有人用了一个比喻,说他们是优步司机,而我们是出租车司机。我说:“好吧,也许吧。但也许你们是优步,而我们是F1赛车手。”
哦,我喜欢这个。
不是要自吹自擂。
哦,抓住这个机会。
优步和法拉利没什么关系。我是一个车迷,对吧?也许优步能帮粉丝们到达赛场,但它不是比赛,对吧?那些技术与比赛无关。我认为这些技术在这一点上非常出色,它们能让下一代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些资源的电影制作人获得接触的机会。
有一代电影制作人永远无法进入好莱坞。我希望好莱坞仍然是文化创造和电影制作的重要中心,因为这些人最终会对提示词式(prompt-based)的电影制作感到厌倦,他们会像我们过去一百年来做的那样,来试图说服别人给他们一些钱,雇佣一个真正的、正式的好莱坞团队,去拍一部真正的电影。
我会提到肖恩·贝克(Sean Baker),一个了不起的电影制作人。在他用iPhone拍摄了著名的《橘色》(Tangerine)之后,第二年我看了《佛罗里达乐园》(The Florida Project),我感到震惊。我当时想:“我必须重新考虑我的全部…… [内容被截断]
🚀 想要体验更好更全面的AI调用?
欢迎使用青云聚合API,约为官网价格的十分之一,支持300+全球最新模型,以及全球各种生图生视频模型,无需翻墙高速稳定,文档丰富,小白也可以简单操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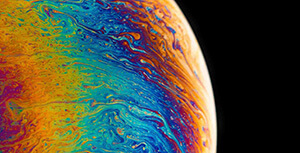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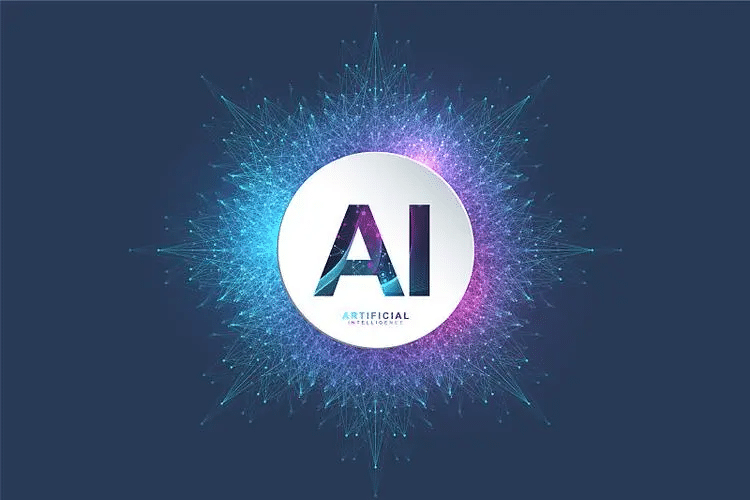

评论区